Geoffrey Hinton是深度學習的創始人之一,2019年圖靈獎得主,谷歌工程研究員。
在津南谷歌的I/O開發者大會上,美國科技媒體Wired的NicholasThompson和Hinton討論了他早期對大腦的癡迷,以及計算機可以模仿其神經結構的可能性。他們還討論了意識這個概念以及Hinton未來的計劃。
以下是對話過程,請欣賞!
Nicholas Thompson:讓我們從你早期的一些極具影響力的論文開始談起。每個人都說,“這是一個聰明的想法,但實際上我們不可能以這種方式來設計計算機。那么,請解釋一下你為什么如此堅持、如此自信地認為自己找到了重要的東西。
在我看來,大腦必須通過學習“聯系”的力量來發揮作用,除此以外沒有別的方式。如果你想讓一個設備完成一些智能工作,那么有兩個選擇:一是你可以編程,二是它可以學習。人當然不是被編程的,所以我們必須學習。因此這肯定是正確的道路。
NT:那么,能解釋一下神經網絡是什么嗎?
GH:你有相對簡單的處理元素,它們是非常松散的神經元模型。這些模型之間有連接,每個連接都有權值,并且可以通過學習改變權值。神經元所做的是,將連接上的活動乘以權值,再把它們全部加起來,然后決定是否發送輸出。如果它得到一個足夠大的和,就會發送一個輸出;如果總和為負數,則不會發送任何內容。僅此而已。你所要做的就是把成千上萬的神經元和成千上萬的權值的平方連接起來,然后算出如何改變權值,它就能做任何事情。這只是一個你如何改變權值的問題。
NT:你是什么時候意識到這種模式與大腦運作方式相近的?
GH:神經網絡總是這樣設計出來的,被設計成像大腦那樣去工作。
NT:意思就是,在你職業生涯的某個階段,你開始去了解大腦的工作方式。或許是在你12歲的時候,也或許是在你25歲的時候。所以,你究竟是什么時候決定要模仿大腦來制作電腦模型的?
GH:基本是在了解大腦原理后。具體想法是:通過改變連接的字符串(就像人們認為的大腦學習方式那樣),來制造一個像大腦那樣學習的學習設備。這個主意也不是我的首創,圖靈也有同樣的想法。圖靈,盡管他奠定了很多標準計算機科學的基礎,他也相信大腦是一個有著隨機權值的無組織的“裝置”,它會使用強化學習來改變連接,最終學習一切。他還認為這是獲得情報的最佳途徑。
NT:所以你遵循圖靈的想法——制造機器最好的方法就是模仿人類的大腦。腦子里想著:這就是人腦的工作原理,因此讓我們造一個這樣的機器吧。
GH:是的,這不僅僅是圖靈的想法,很多人都這么認為。
NT:最黑暗的時刻是什么時候?還有,什么時候那些同樣贊成圖靈想法、一直在工作的人退縮時,但你卻仍然繼續前進?
GH:總有一群人始終相信它,尤其是在心理學領域。但是對于計算機科學家,90年代時得到的數據集非常小,計算機運行也沒有那么快。在小數據集方面,其他的方法比如支持向量機,工作得更好。
在80年代我們就發展了反向傳播,原本以為它能解決所有問題,結果卻不行,我們疑惑為什么行不通。現在知道其實是數據規模導致其不能解決所有問題,當時我們都沒有意識到。
NT:那你當時認為為什么行不通呢?
GH:我們認為這行不通,是因為我們沒有完全正確的算法和完全正確的目標函數。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一直認為這是因為我們一直在做監督學習,你必須給數據貼上標簽。其實我們應該做的是無監督學習,就是從沒有標簽的數據中學習。
NT:有意思。所以問題是你沒有足夠的數據,而你當時卻以為自己擁有適量的數據,但未被正確標記。因此你只是誤解了這個問題?
GH:我認為僅僅使用標簽是一個錯誤。大部分學習過程都沒有使用任何標簽,只是嘗試在數據中對結構建模。我相信這一點。我也認為隨著計算機變得越來越快,對于任何給定大小的數據集,只要計算機足夠快,都最好做無監督學習。一旦你完成了無監督學習,你就能從更少的標簽中進行學習。
NT:所以在20世紀90年代,你仍然繼續身處學術界進行這個研究,也依舊發表論文,但沒有解決什么大的問題。你有沒有說過,我覺得研究夠了,要去試試別的方向?還是你只是堅持要繼續研究深度學習?
GH:是的,我一直在堅持這樣的研究一定有用。我的意思是,大腦中的連接正在以某種方式完成學習過程,我們必須弄清它。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方法來學習連接的強度,大腦正在使用其中一個。當然,你也必須擁有可以學習這些連接強度的東西。我從來沒有懷疑過這一點。
NT:因此你永遠不會懷疑。那么,什么時候研究開始可行的?
GH:80年代最令人沮喪的一件事是,如果你建立的網絡有很多隱藏層,你就無法訓練它們。這也不完全正確,因為你可以訓練一些相當簡單的任務,比如識別筆跡。但是大多數深層神經網絡,我們是不知道如何訓練它們的。大約在2005年,我想出了一種無人監督的深網訓練方法。你獲取到輸入,比如說像素,然后你會得到一堆特征,它們很好地解釋為什么像素是這樣的。接著你把這些特征當做數據,又學習到另一組特征,所以我們可以解釋為什么這些特征有相關性。你不斷地進行一層又一層學習,但有趣的是,你可以通過一些數學運算,來證明每次你學習另外一層,你不一定有一個更好的數據模型,但你有一個關于你的模型有多好的波段。這樣每次添加另一層時,你都可以獲得更好的波段。
NT:這是什么意思,你有一個關于你的模型有多好的波段?
GH:一旦有了一個模型,你說,“模型找到這些數據有多令人奇怪?”你向它展示了一些數據然后說:“這是你相信的那種東西嗎,還是說這令人驚訝?”而你想要做的是擁有一個模型,一個好的模型是看著數據說,“是的,是的,我知道。這是不足為奇。”
通常很難準確計算出這個模型發現數據的驚人程度。但是你可以在上面計算一個波段,然后得出結論說這個模型發現的數據沒有那個模型那么令人驚訝。你還可以展示,當添加了額外的特征探測器層時,得到一個模型能使得你每次添加一個層,波段就會發現數據變得更好。
NT:大約在2005年,你取得了這個數學上的突破。那么你又是什么時候開始得到正確答案的?當時你在處理什么數據?你在處理什么數據?語音數據是你的第一個突破,對吧?
GH:這只是手寫的數字,非常簡單。而之后大約在同一時間,他們開始開發GPU(圖形處理單元)。大約在2007年,做神經網絡的人們開始使用GPU。我有一個非常優秀的學生,也開始使用GPU來尋找航拍圖像中的道路。他寫了一些代碼,然后被其他學生用來使用GPU去識別語音中的音素,當時他們正在使用預訓練的想法。在他們完成所有這些預訓練之后,只要把標簽貼在上面然后使用反向傳播,你就可以有一個經過預訓練的非常深的網。然后你可以繼續使用反向傳播,它確實有效。它在某種程度上超過了語音識別的基準。
NT:它擊敗了最好的商業語音識別?也擊敗了語音識別方面最好的學術工作?
GH:在一個名為TIMIT的相對較小的數據集上,它的表現略好于最好的學術作品。還在IBM完成了工作,并且相當迅速。很快,人們就意識到這個東西——因為它打敗了花了30年時間開發的標準模型——如果再多開發一點就會做得很好。所以我的研究生們去了微軟,IBM和谷歌,谷歌是最快把它變成生產語音識別器的。到2012年,這項2009年首次完成的工作,在Android上出現了。而后Android在語音識別方面突然變得更加擅長。
NT:自從40年前開始產生這個想法的那一刻,你已經研究了20年,現在你終于比你的同事出色了。這種感覺怎么樣?
GH:我只有30年的想法!
NT:是的,是的!所以只是一個新想法。新的!
GH:我感覺很好,它終于找到了真正的問題所在。
NT:你還記得第一次得到啟示性的數據時,你在哪里嗎?
GH:不記得了。
NT:好的。所以你意識到它適用于語音識別。那又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將它應用于其他問題?
GH:就在那之后我們開始把它應用到其他各種問題上。George Dahl是最早從事語音識別研究的人之一,他將其應用于預測一種分子是否會與某種物質結合,并成為一種良好的藥物。還有這么有一場比賽,他只把我們設計的語音識別標準技術應用到預測藥物的活性上,就贏得了比賽。表明了這些東西的運用范圍是相當普遍的。然后我的一個學生說,“Geoff,你知道么,這個東西將用于圖像識別,李菲菲已經為它創建了正確的數據集。還有一個公開的競爭,我們也必須這么做。”
當時是2012年,我們得到的結果比標準的計算機視覺要好得多。
NT:那么,是什么區分了哪些區域工作最快,哪些區域需要更多間?似乎視覺處理、語音識別,這樣類似于用感官知覺來處理的人類核心活動被認為是首先需要清除的障礙,對嗎?
GH:是也不是,因為還有一些比如運動控制這樣的其他領域。我們人類非常擅長運動控制,我們的大腦顯然就是為此而設計的。而直到現在,神經網絡才開始與其他最好的技術競爭。神經網絡技術最終會贏,但現在才剛剛開始贏。
另外,我認為推理——抽象推理,這是我們要學習做的最后一件事,我也認為這將是神經網絡學習做的最后一件事。
NT:所以你一直說神經網絡最終會贏得一切。
GH:嗯,我們都是神經網絡。他們可以做任何我們能夠做的事情。
NT:是的,但是人腦并不一定是有史以來最有效的計算機器。
GH:當然不是了。
NT:當然不是我這人類的腦袋!難道不存在一種比人腦更有效的機器建模方法嗎?
GH:從哲學的角度來說,我并不反對這樣的想法,即可能有一些完全不同的方式來做出(人類能夠做到的)這一切。比如它可以是這樣的。如果從邏輯開始,你試圖將邏輯自動化,然后再做一些看起來很酷炫的定理證明,再做些推理,然后你決定通過推理來做視覺感知——可能最后成功方法就是這個。事實證明它沒有。但我對這一事實沒有哲學上的反對意見。只是我們知道大腦可以做到這一點。
NT:但也有一些事情我們的大腦做不好。對于這些事情而言,神經網絡會不會也沒有什么辦法將其做好呢?
GH:很可能(做不好),是的。
NT:我這還有個相對獨立的問題:我們并不完全知道它們到底是如何運作的,對吧?
GH:不,我們確實不知道它們如何運作。
NT:我們不了解自上而下的神經網絡是如何工作的。這是我們不理解神經網絡運作方式的一個核心要素。麻煩您解釋一下這個問題,然后讓我再問一下這個顯而易見的跟進問題:如果我們不知道這些東西是如何工作的,那它們怎么能起作用呢?
GH:如果你看一下目前的計算機視覺系統,其中大部分基本上是前饋;他們不使用反饋連接。當前的計算機視覺系統還有一個問題——它們很容易出現對抗性錯誤。你可以稍微改變一張熊貓照片上的幾個像素——現在照片看起來仍然像只熊貓,但系統會突然改口說這其實是一只鴕鳥。顯然,你改變像素的方式是經過精心設計的,從而欺騙它認為照片是一只鴕鳥。但重點是,照片對你來說仍然像一只熊貓。
最初我們認為這些算法非常有效。但是,當我們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事實,即他們明明面對著一只熊貓但確信這其實是一只鴕鳥時,你會有點擔心。我認為這個問題一部分是由于,這些算法不是試圖從概括性表征中重建圖像,而是試圖進行歧視性學習。在那里你只學習特征探測器的層次,而目標函數只是關于改變權重以便你更好地得到正確的答案。
最近在多倫多,我們一直在發現,或者Nick Frost一直在發現,如果你引入重建,那么它可以幫助你更好地解決對抗性攻擊這一問題。所以我認為在人類的視覺中,我們使用重建來進行學習。并且,因為我們通過重建來進行大量學習,我們更不易于被對抗性攻擊蒙蔽雙眼。
NT:你相信神經網絡中的自上而下的信息傳導旨在幫助你測試如何進行重建。你如何測試并確定它是熊貓而不是鴕鳥?
GH:我認為這至關重要,是的。
NT:但是腦科學家并不是很贊同這一觀點是嗎?
GH:腦科學家們都同意這一表述——如果你在感知途徑中有兩個皮質區域,那么一定會有向后的連接。這些科學家們在其用途上懷有不同的觀點。有人認為這可能是為了關注,可能是為了學習,也可能是為了重建。或者它可能包括所有這些可能性。
NT:所以我們并不知道向后溝通是什么。您正在將重構組合進您構建的神經網絡(或向后溝通)中,即使我們不能夠確定那就是大腦的運作方式?
GH:是的。
NT:這不是作弊嗎?我的意思是,你是想做一個與大腦一樣的東西,但你目前壓根不知道大腦是如何運作的。
GH:并不是。我不是在做計算神經科學。我也不是想模擬大腦的運作方式。我其實是被大腦激發靈感,說“這玩意能用,如果我們想做些什么類似有效的東西,我們應該從這里來找靈感。“。
所以這是”神經啟發“,而不是神經模型。整個模型,包括我們使用的神經元,都是受到神經元有很多層聯系并且此聯系的強度能夠被改變這一事實的啟發。
NT:這很有趣。那么如果我從事計算機科學,而且我正在研究神經網絡并想要擊敗你,那么一種選擇就是建立自上而下的溝通機制,并將其建立在其他腦科學模型上。所以是基于學習而不是重建。
GH:如果他們確實是更好的模型那么你就贏了。就這樣。
NT:那真是非常有趣。讓我們轉到更一般的話題吧。這么說來,神經網絡將能夠解決各種問題。那么有沒有神經網絡無法捕獲的人類大腦的奧秘?例如,情緒......
GH:不。
NT:那么愛可以通過神經網絡重建嗎?意識可以重建嗎?
GH:當然。一旦你弄明白這些東西意味著什么。我們是神經網絡,對吧?意識是我特別感興趣的東西。沒有它我還是能活下來,但......人們并不真正知道它們的含義。有各種不同的定義。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科學的術語。100年前,如果你問人們什么是生活,他們會說,“生物有生命力,當它們死亡時,生命力消失了。這就是活著和死亡之間的區別,即你是否具有生命力。
“現在我們不再有生命力這一表述了,我們只是認為這是一個科學發展前的偽概念。一旦你學習一些生物化學和分子生物學,你就不再需要生命力這一解釋了,你將能夠理解它是如何運作的。我認為這與意識相同。我認為意識是一種用某種特殊本質來解釋心理現象的嘗試。
而這個特殊的本質,你其實并不需要它。一旦你能夠真正解釋它,那么你將能夠解釋我們如何做出那些讓人們認為我們具有意識的行為,你也將能夠解釋所有這些不同的意識含義——完全不需要借助于什么‘意識’這一概念。
NT:所以沒有無法創造的情感?無法創造的思想?一旦我們真正理解了大腦是如何工作的,那么在理論上,人腦所有的功能都能夠被一個完整構造的神經網絡所執行?
GH:約翰列儂有一首歌,聽起來很像你剛才所說的情況。
NT:你對此有100%的信心嗎?
GH:不,我是貝葉斯派,所以我有99.9%的自信心。
NT:好的,那0.1是什么?
GH:那是說,比如,我們所有人、所有這些都是一個龐大模擬的一部分。
NT:那倒是不假。那么我們從計算機工作中學到了什么呢?
GH:所以我認為我們在過去十年中所學到的是,如果你采用一個具有數十億個參數的系統,以及一個目標函數——就像用文字填補空白一樣——它將能夠比你預期的更加完美地運行。您可能會想到(傳統AI學派中的大多數人也都會這么想),采用具有十億個參數的系統,用隨機值啟動它們,測量目標函數的梯度(即對于每個參數,如果你稍微改變一下這個參數,看目標函數將如何變化)——然后在改善目標函數的方向上改變它。
你可能會覺得這將是一種陷入困境的無望算法。但事實證明,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算法。你越將其規模擴大,它就越好。這真的只是一個實踐上的發現。確實有一些相關理論出現,但它基本上算是一個實踐發現。現在,因為我們已經發現了這一點,它使得”大腦計算某些目標函數的梯度,并更新突觸強度的權重以遵循該梯度“這一猜想更加合理。我們只需弄清楚它如何進行降級,以及目標函數是什么。
NT:但我們當時對大腦并不了解吧?我們并不了解重新加權?
GH:這曾是一個理論。很久以前,人們認為這是一種可能性。但總會有一些傳統的計算機科學家說:“這一切都是隨機的,你只需通過梯度下降來學習它——這對于十億個參數來說永遠不會有用。你必須掌握很多知識。“我們現在知道這是錯的;你可以隨便輸入起始參數,并學習一切。
NT:所以讓我們把它擴展一下。當我們在模型上運行這些大規模測試時,根據我們對人類大腦功能的理解,我們可能會繼續越來越多地了解大腦實際上是如何運作的。你認為這會最終導致這樣一種情形嗎——我們將人類大腦重新連接成更高效的機器?
GH:如果我們真的了解現狀,我們應該能夠讓教育工作變得更好。我覺得我們會的。如果你最終能夠了解你的大腦中發生了什么并且它如何進行學習,但你卻無法為更好進行學習而適應環境,那真的是非常奇怪。
NT:未來幾年內,您認為我們將如何利用我們對大腦的了解以及深度學習改變教育的運作方式?您會怎么改變教學課程?
GH:幾年后,我不確定我們會學到多少東西。我認為改變教育的時間會被拖長。但是你可以看到現在的(機器人)助手正在變得越來越聰明。一旦它們能夠真正理解對話,就可以與孩子進行對話并對他們進行教育。
NT:理論上,當我們更好地理解大腦時,你會根據我們知道他們將要學習的方式,讓助手們與孩子們進行更好的對話。
GH:是的,我對此并沒有太多考慮。這不是我的研究內容,但聽起來確實很可信。
NT:我們將能夠理解夢是如何運作的嗎?
GH:是的,我對夢超級感興趣。我至少有四種不同的做夢理論哦。
NT:讓我們聽一聽唄,一,二,三,四。
GH:很久以前,有一些叫做Hopfield網絡的東西,它們把記憶當做本地吸引子來學習。Hopfield發現,如果你試圖把太多的記憶放進去,它們就會感到困惑。它們會把兩個本地吸引子同時考慮進來并將其合并為二者之間的某種吸引子。
然后,Francis Crick 和Graeme Mitchison發現,我們可以通過”忘卻“來擺脫這些假極小值。因此我們關閉輸入,將神經網絡置于隨機狀態,然后讓它穩定下來。我們覺得這很糟糕,改變連接,這樣你就不會一直穩定于那個狀態。如果你這么做了的話,網絡就能夠存儲更多的記憶了。
然后我和Terry Sejnowski反應過來:如果我們不僅有幫助儲存記憶的神經元(姑且稱之為名花有主的神經元),我們還有一些其他富余的神經元(姑且稱之為形同單身的神經元),我們是否能夠找到一種算法,能讓這些富余的神經元也來協助存儲記憶?
最后,我們想出了Boltzmann機器學習算法,它有著非常有趣的屬性:輸入數據,它在其他節點周圍搖搖晃晃,玩到開心為止。一旦完成,它會基于兩個單元節點是否處于激活(active)狀態來增加所有連接的強度。
你還必須歷經一個階段:切斷神經元的輸入,你讓它四處游蕩并進入一個它滿意的狀態,當它玩爽了,你說:“把所有的活躍分子(激活的神經元)逮出來不讓它們坐一塊(減弱連接強度)”。
所以這里我這里在介紹玻爾茲曼算法的步驟。但實際上,這個算法背后有著深厚的數學背景,你在處理的問題,無非是如何改變連接關系,使得有著這些隱藏單元(hidden unit)的神經網絡能夠清楚地復現數據。同時,這個算法中,必須還有另一個階段,我們稱之為負面階段。在網絡沒有輸入的情況下運行時,它會“忘記”之前所有的狀態。
我們每晚都要做好幾個小時的夢。如果我隨機叫醒你,你可以告訴我你剛剛夢到了什么,因為夢的信息都儲存在你的短時記憶力。沒錯,你做了好幾個小時的夢。
但是當你早上醒來時,你經常只能回憶起一串夢中的最后一夢,別的都想不起來了——這是件多么幸運的事情啊,因為夢的記憶越多,現實的記憶也會越少,你會無法分辨一段模糊的記憶究竟是真實發生的,還是夢里浮現的。那么,為什么我們不能夠記得我們夢里發生的所有事情呢?Crick的觀點是,夢的全部意義在于忘掉那些事情,這就如同你把所有學過的東西都還給老師了。
而Terry Sejnowski和我證明,實際上,這便是Boltzmann機器的最大似然的(maximum-likelihood)學習邏輯。這和做夢一樣。
NT:我想談談你的其他理論。但是你在設計深度學習算法時,真的基于了夢的模式嗎?研究圖像數據集一段時間,重置,再次研究,再重置。
GH:是的,我們有些類似的機器學習算法。最早一些可以學習如何處理隱藏單元的算法都是基于Boltzmann機,但是它們效率很低。不過,我發現了一種對它們進行近似的方法,提高了它們的效率。這個方法才是把深度學習救回正軌的東西。那個方法就是限制性Boltzmann機的有效表述形式,它所做的,就是忘記學習過的一切。但是,這個神經網絡不是真的在全程睡覺劃水,它只是在運算完每個數據點之后,小小地走神一下。
NT:好的吧,所以這些機器人會做夢,夢里還在數山羊。我們接著來看看第二,第三和第四條理論吧。
GH:第二理論被稱為睡眠喚醒算法(Wake Sleep Algorithm)。你的目的,是得到一個生成模型。所以你會想到,你想擁有一個可以生成數據的模型,這個網絡模型里有著多層的特征檢測器,并能夠從高到低激活從高級到低級的特征,直到它直接激活了像素數據(輸入數據)——像素數據就是圖片的基本表述方式。你也當然想反向開車,你想做圖像識別。
因此,你就有了一個由兩個階段組成的算法。在喚醒階段,數據輸入,神經網絡做圖像識別,不是學習用于識別的連接,而是學習生成連接。 所以數據進來,我激活了隱藏單位。
然后我學會讓那些隱藏的單位善于重構那些數據,因此它正在學習在每一層進行重構。問題在于,你如何學習前向連接?我的想法是,如果你知道前向連接,你可以學習后向連接,因為你可以學習重建。
現在,事實證明,如果使用后向連接,你可以學習前向連接,因為你可以從頂部開始生成一些數據。由于你生成了數據,你知道了所有隱藏層的激活狀態,因此您可以學習前向連接來恢復這些狀態——這就是睡眠階段。當你停止輸入時,你只需生成數據,然后嘗試重建生成數據的隱藏單位。因此,如果你了解了自上而下的連接,你也將學習自下而上的連接。
如果你知道自下而上的那些連接,你會學到自上而下的連接。(譯者:個人理解,假想模型神經網絡前向傳播是一套權值,反向傳播是另外一套權值,其一可知其二。)那么,如果你從隨機的連接開始,并嘗試交替使用兩者,會發生什么呢?嘿,居然真的還能用。當然,為了更好的效果,你必須做各種調整,但是交替使用確實能用。
NT:好的吧,那你準備介紹一下另外2個理論嗎?我們還有8分鐘,是不是也許我們先問其他的問題?
GH:如果你再給我一個小時,我就能把另外2個家伙搞出來。
NT:好的吧,那我們還是來談談下一個話題吧。你接下來的研究是什么?你現在準備解決什么問題?
GH:你最終想做的,還是那些你沒有完成的事情。我認為我可能會研究我從未完成的事情,我稱之為膠囊網絡,它是關于如何使用重構進行視覺感知的理論,以及如何將信息規劃到正確的位置。在標準神經網絡中,信息,網絡層的活性,只是自動地存儲;你不能決定將它們發送到哪里。膠囊網絡的理念是決定在哪里發送信息。
現在,自從我開始研究膠囊網絡以來,谷歌的其他一些非常聰明的人發明了transformer,transformer正在做和膠囊網絡同樣的事情。transformer決定在哪里路由信息,這是一個巨大的突破。
推動膠囊網絡發展的另一動力是坐標系。當人類使用視覺時,他們是在使用坐標系的。如果它們在對象上使用了錯誤的坐標系,那么他們甚至無法識別該對象。給你舉一個小栗子:想象一個四面體;它有一個三角形底座和三個三角形面,所有等邊三角形。容易想象,對嗎?現在想象一下用一個平面把它切開——你看到了一個正方形截面。
這就不容易想到這個對象其實是個四面體了吧,對吧?每次切片時,你通常都會得到一個三角形的截面。如何獲得一個正方形的截面,并不好想。不,可能這一點都不好想。好的,但我會幫你得到這個詭異的形狀。我需要你的筆。想象一下,如果你拿這樣的筆,你會得到這樣的形狀,另一支像這樣的直角筆,你將這支筆上的所有點連接到這支筆上的所有點。那是一個堅實的四面體。
好的,你看到它其實是另外一套坐標系,四面體的邊緣,這兩條線和坐標系的標線重合。如果你用那一套坐標系想象一個四面體,很明顯,這樣,在頂部你有一個長方形,在底部我們也得到一個長方形,中間有一個正方形。所以現在很清楚了,你如何切割它能夠得到一個正方形的截面,前提是你參考的是什么坐標系。
因此很明顯,對于人類而言,坐標框架對于感知非常重要。
NT:但是你是如何在你的模型中加入參考系信息的呢?我的意思是,你是如何改正了你在1990年代犯的錯誤:嘗試把規則帶入系統中卻使之與系統非監督學習的本質產生矛盾?
GH:你對這個錯誤的總結非常到位。我太固執了以致于這變成了一個大錯誤,我現在就想彌補一點過失。這有點像尼克松總統當年與中國談判一樣。實際上,我在這個事情上,發揮了不好的作用。
NT:所以你現在的工作主要是針對于視覺識別,還是可以看做提高當前坐標系規則的研究?
GH:這個技術當然能用在其他領域里,但是我的興趣主要在于怎么把它用在視覺識別上。
NT:深度學習曾經是一個獨特的東西,我的意思是,深度學習是深度學習,人工智能是人工智能(AI)。現在,深度學習變成了AI的同義詞,同時現在AI變成了熱門的營銷術語,基本上意味著以某些方式驅動機器。作為幫助創建這一術語的人,您是如何看待這個現象的?
GH:曾幾何時,人工智能,意味著邏輯主義/符號主義,研究人員用計算機的符號字符串模擬人類的認知。還有神經網絡,就意味著你在使用神經網絡進行學習。不同的企業,不同的學派,百家爭鳴,大放異彩。這就是我當年成長的環境。而現在我看到好多人一邊常年一直在說神經網絡就是廢物,一邊又在說“我是人工智能專業的教授,我需要錢”。這就很煩人。
NT:嗯,我還有時間,就再問一個問題。在一次采訪中,談到人工智能,你說,好吧,把它想象成一個反鏟——一個可以挖坑的機器,用的不好就會傷到自己。解決問題的關鍵是,當你準備使用反鏟作業時,要好好看著準備挖坑的鏟子和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不要讓鏟子碰了腦袋。 對于你的工作而言,你做出的什么選擇和這個例子很接近?
GH:我猜我永遠不會主動應用人工智能技術制造武器。我的意思是,你的確可以設計出功于殺戮的反鏟。但是我覺得這一定是反鏟最差勁的應用了,我永遠不會干這事的。
NT:好的,Geoffrey Hinton。這真是一場令人印象深刻的訪談。滿滿的都是干貨。我們“明年”還會回來的——帶著第三和第四的“做夢”理論。
-
神經網絡
+關注
關注
42文章
4781瀏覽量
101176 -
人工智能
+關注
關注
1796文章
47683瀏覽量
240302 -
深度學習
+關注
關注
73文章
5516瀏覽量
121553
原文標題:Geoffrey Hinton專訪:如何解釋神經網絡的變遷
文章出處:【微信號:BigDataDigest,微信公眾號:大數據文摘】歡迎添加關注!文章轉載請注明出處。
發布評論請先 登錄
相關推薦
【專輯精選】人工智能之神經網絡教程與資料
基于賽靈思FPGA的卷積神經網絡實現設計
深度神經網絡是什么
卷積神經網絡模型發展及應用
綜述深度神經網絡的解釋方法及發展趨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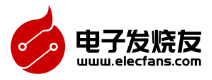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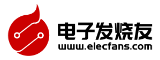


 深度學習的創始人解釋了神經網絡的變遷資料說明
深度學習的創始人解釋了神經網絡的變遷資料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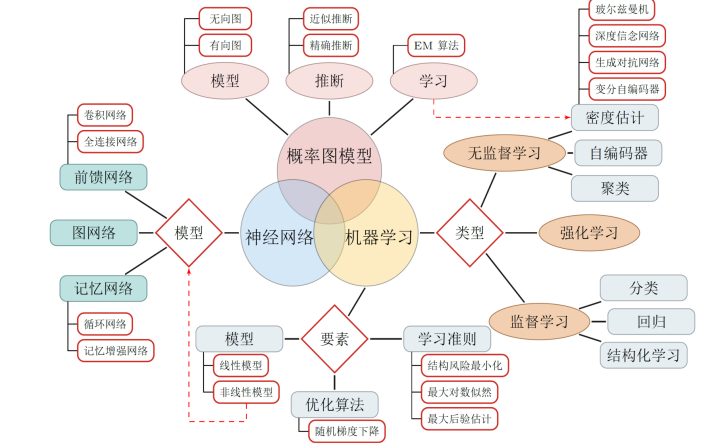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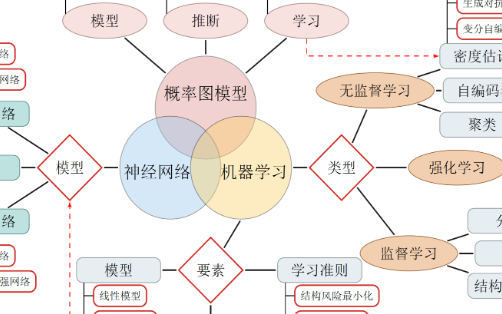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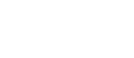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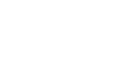





評論